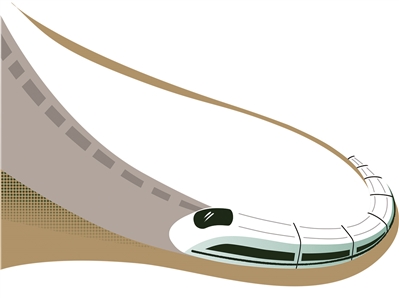
■资料配图
凌晨两点,城市才在白天的喧嚣过后迎来一线寂静。叶升弯腰钻进竖井步梯前,提着边缘漆面磨损安全帽的指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,但随即就被沾染着柴油、铁锈与土腥味儿的气息裹挟起来。
“升哥,2号盾构机参数异常!”隧道距地面垂直落差数十米,还未等到叶升抵达轨行区,对讲机里传来助理工程师周林急促的声音,瞬间刺破了夜的安静。再往下的二十米开外,盾构机庞大的身躯微微震颤,刀盘发出丝丝尖锐的摩擦声,暗红色的泥浆随即顺着管片缝隙渗出,在地面积成蜿蜒的小径。
经验告诉叶升,情况紧急。十年前基坑涌砂事故,也正是砂水倒灌让整个工程滞后半年,还给市民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此情此景,正逐渐与记忆中模糊的警报声重叠。“要尽快处理,一刻也不要耽误!”叶升一边通过讲机传达指令,一边疾步下行,沉重的脚步与厚实的铁片碰撞出一连串的“咚——哐当”声。
“启动二次注浆预案!”应急小组前脚接后脚赶过来时,叶升的吼声已在隧道里形成一种坚定的回音。叶升带着应急小组抬起沉重的钢梁,一点一点地往隧道顶部搭建支撑结构。时值深秋,地下却宛如巨大的蒸笼,闷热潮湿,汗水不停地从他们的额头、脸颊滑落,模糊了双眼,浸透了衣衫。但没有一个人退缩,地铁建设牵一发而动全身,危险就像一颗种子,只有将之扼杀在萌芽前才能确保安全。
与此同时,地面小组也正绷紧神经,跟着叶升的指引通过钻孔设备将加固材料缓缓注入地下。凌晨五点,地面沉降数据终于趋于稳定,隧道内闪动红色警报灯随之切换为平和的色调。城市在酣睡中缓缓醒来,一切如常,除了叶升和工友,不会有人知晓这个夜晚的惊心动魄,而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。
“升哥,安全了吗?”周林捧着图纸的双手还在抖动,手套早被油渍和泥水浸透成黄铜色,这个刚毕业的轨道交通专业高材生在此之前还不曾见过真正的险情。经此一役,他也将成长几分。
“知道为什么管片要设计成六边形吗?”叶升轻拍周林的肩膀,用力在疲倦的脸上挤出欣慰的笑容,“每个环要承受六向压力,我们也一样,只有时刻不松懈才能确保安全。”
六点整,当第一抹洒在珠江的晨曦搅起鳞状的波光时,叶升回到地上。阳光焯去地下的昏暗,他一度觉得白昼的景色有些许陌生。也是不久前的某天,线路施工关键节点顺利攻坚后的清晨,妻子带着五岁的女儿来工地送早饭,双手护着的保温桶还冒着皮蛋瘦肉粥的热气。“爸爸的火车为什么总在晚上开?”女儿尚幼,自然不知盾构机为何物,也还难以理解这份总在地下角落坚守的工作。不知怎的,这个经历过数条地铁新线建设全过程的硬汉在一刹那红了眼眶。
十五年间,他从初来乍到的青涩小伙,成长为技术娴熟的一线骨干,如同其他同事,就像一颗坚定的铆钉,牢牢地“钉”在这片土地上,也深深爱上了这座充满烟火气与拼搏劲儿的城市。作为一名父亲,他难免有所愧疚;可作为一名地铁建设者,他始终满怀骄傲。初入行时,带教师傅谈起“当年那些卡我们脖子的德国工程师”的愤懑与遗憾还言犹在耳,如今,他和新人周林提及的已经是铿锵自信的“自主研发”“国产盾构”。叶升清楚,这份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地下,更体现在地上。
“熬了一晚上,快来喝点猪脚姜暖暖身子!”食堂黄姨的吆喝打断了叶升的遐想,她已连续7天为夜班工人熬制广式糖水。黄姨其实不必多做功夫,但她说:“你们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。”
叶升端起热腾腾的姜汤,心里念着回家后要给女儿一个温暖的拥抱:“等隧道亮起通车的明灯,爸爸让你坐上最安全的地铁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