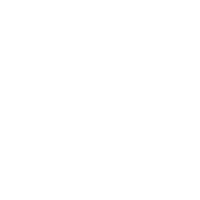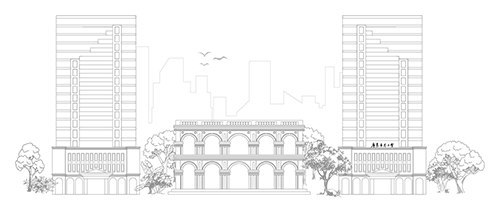清晨七点多,阳光刚爬上窗棂,生物钟就把我唤醒。老公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嘟囔:“放假也不睡个懒觉,吵得人睡不好。”我边叠被子边笑:“老话说得好,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”这话从记事起就听母亲念叨,如今早已成了刻进骨子里的习惯。
小时候在老家,母亲就是家里的“活闹钟”。每天,天还没亮透,厨房柴火已噼啪作响,饭菜的香气飘进屋子,母亲就会挨个儿敲我们房门:“该起床了,别学懒虫!”那时,总觉得被窝暖和,磨磨蹭蹭不想动,母亲就会掀开被子,把我们拽起来。渐渐地,我们兄弟姐妹都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,哪怕寒暑假,也没睡过几次懒觉。
母亲这辈子就没闲下来过。寻常的春日,晨雾还没散尽,母亲就已扛着锄头往田里去。红土地板结得像石块,她弓着背,一锄一锄地刨,额头的汗珠顺着晒黑的脸颊滚落。正午的太阳把大地烤得发烫,别人都躲在家里休息,她却顶着烈日给新播的菜苗浇水,龟裂的手掌紧紧攥着水管,被晒得脱皮的脖颈泛起一层层盐霜。
到了夏天,太阳毒辣得能把人晒化。母亲凌晨四点就摸黑起床,踩着露水去菜园摘菜。豆角、茄子挂满藤蔓,她踮着脚、猫着腰,不一会儿竹篮就沉甸甸的。回家简单扒拉两口早饭,又推着装满蔬菜的三轮车往集市赶,在闷热的摊位前一站就是大半天。傍晚收摊回来,顾不上擦汗,又钻进厨房给全家做饭,灶台腾起的热气裹着油烟,熏得她直咳嗽,却还是哼着小曲儿忙个不停。
冬天寒风刺骨,母亲的手被冻得通红开裂,可她依旧闲不住。天不亮就去溪边洗衣服,冰凉的溪水浸透手套,手指冻得像胡萝卜。晾晒完衣物,她又开始准备过冬的腌菜,切萝卜、拌辣椒,一忙就是大半天。她总说:“趁冬天干爽多准备些,开春忙起来就没工夫了。”就连晚上,她也要接些糊火柴盒、缝鞋垫的手工活,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到深夜。
在母亲的影响下,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手脚勤快。上大学后,我利用课余时间做过酒店服务员、发过传单、当过家教。在酒店端盘子时曾手忙脚乱,发传单常被路人拒绝,做家教备课到深夜,但每次想放弃时,我总会想起母亲在地里劳作的身影,咬咬牙就坚持下来了。
现在成家了,我依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,周末也会主动收拾屋子、打扫卫生。老公总笑我“闲不住”,可我知道,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宝贵财富。劳动早已不是负担,而是一种本能。“五一”将至,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,我更加怀念母亲,也希望能把这份勤劳的家风传给下一代,让孩子们懂得:只有脚踏实地地付出,才能收获生活的甘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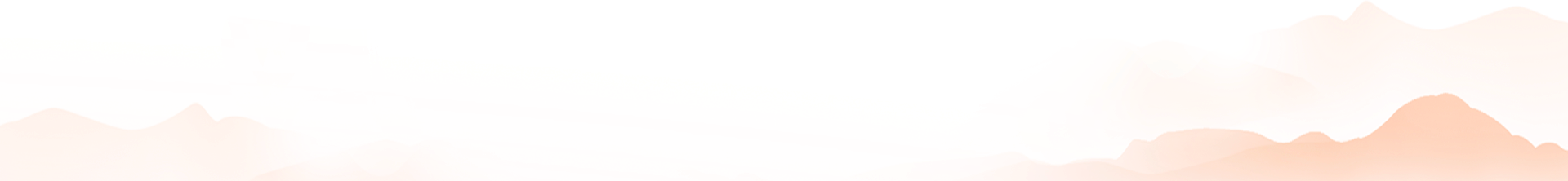




 首页
首页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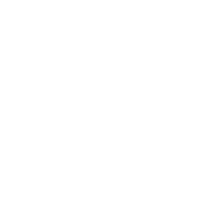
 放大
放大 上一版
上一版